
作者半斤,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半斤八两抡电影”
<内嵌内容,请到原网页查看>
(《春节序曲》——影片中1990年电视访谈的配乐)
一九八零年代,民间兴起外星生命探索热潮,很多人以自己的方式捕捉UFO的痕迹,声称能与地外生命交流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另有一股隐秘在公众视线背后的热潮也在民间萌发,碰撞出星火,那是诗歌的年代。一九八零年,随着《今天》被迫停刊,以及多股诗歌派别和风格的崛起,中国的诗歌创作与交流,在民间焕发出野蛮生长的力量,“新诗潮”标志着中国现代诗内生出了纯文学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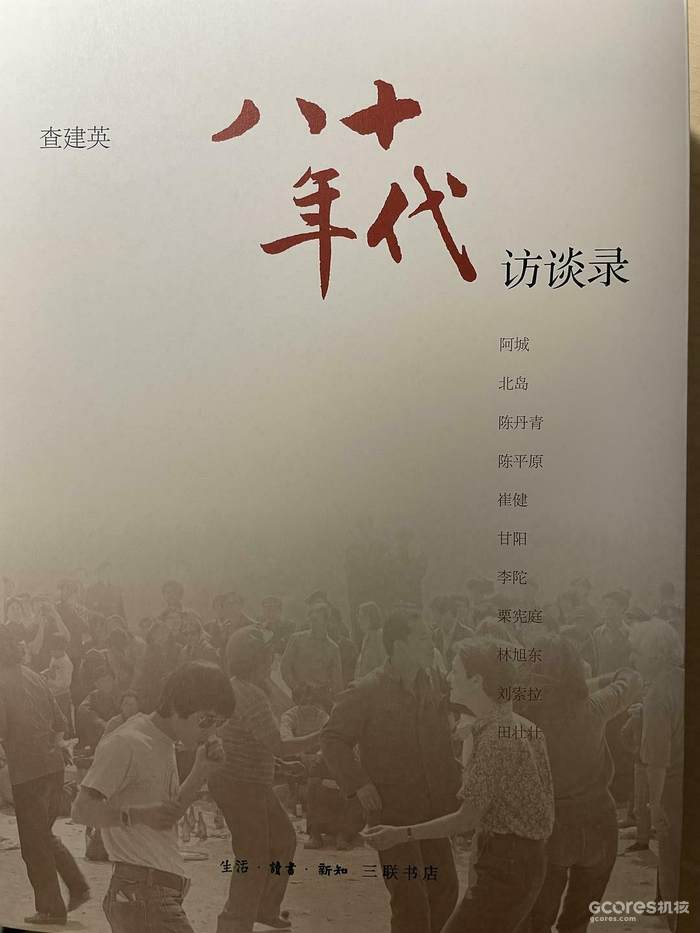
《宇宙探索编辑部》序章,某电视台采访录像里,清晰标识着“1990年”的时间点,指向了那一个民间探索的狂热年代。主角唐志军,其人生的“高光”时刻,永久被记录在那个年代,此后日趋黯淡。在影片的叙事主部,时间被忽略了三十年,唐志军的英姿勃发已成风中残烛,他在录像中的激昂意气萎顿在旧楼陋室中,被视为一个民科的疯癫自噫。唐志军被定格在一九九零年,代表了民间探索的没落,在三十年后的被视为怪诞癫狂的行径反衬下,唐志军们的言行只能存活于一九八零年代。可以说,被叙事跳过的三十年,是唐志军们的八零年代的哀歌,社会潮流每向当下冲击迫近一米,唐志军们的生命力就流失一年。直到他身穿“不严谨”的宇航服被吊车送上半空,在其后的斩首般的电锯切割下,唐志军们被时代杀死,永远活在八零年代。只差一篇墓志铭,在嘲讽中贱卖了宇航服,他们上路了。与其说是探索之旅,不如说是走向终结的告别之旅,唐志军在笔记本上书写的每一笔,都是他刻下的八零年代的墓志铭。

唐志军一行四人的西行,刚好呼应了被多次强化的《西游记》取经组的视觉形象,少了悲壮,被赋予了鸡毛蒜皮的斤斤计较。西行,看似是寻找外星文明到访的痕迹,实则是寻回失落的自我。四人各自以“伪纪录”的访谈形式,对着镜头絮叨了自己的上路动机,这一荒诞的登场方式,令他们“出格”的行为得以自洽。他们的诉说对象,是银幕前的观众,他们在解释各自的行为,为自己反常的、挑战世俗价值的举动辩解,进而拉上了观众作见证,这是对院线观众的照顾,也是对当代价值标准的妥协。唐志军要寻找的“证据”,在影片中是一个活人,不谙世事的男青年——孙一通。有趣的是,唐志军以“科学”语汇组织好的问题,抛给孙一通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一直不屑一顾的艺术——诗的言语。在乡村广播站、在村里的空房中、在田间的泥泞上,一种失落的民间探索悄然被转化为另一种失落的民间运动:寻找外星生命的叙事线被拴在了诗人的身上,确定性寄托给暧昧性,民间科学不得不追索庶民艺术的迷乱步伐。

孙一通的言语看似疯癫,却总如“先知”般应验,日蚀遮蔽天光,麻雀裹盖石狮,他怀揣着的字典是最质朴的言语之书,剥离掉一切功利和贪欲,超越了所有的迷信和权威。孙一通的晕头转向,正是村领导嘴里的“导向”。唐志军再上路,遵循的不再是所谓的“科学”,而是“不可说”的诗人之手。

直到唐志军独自涉险,骑上毛驴,他已经不再是杂志的主编,也不是失职的父亲,更不是当下消费社会的失败小丑。他是骑驴去圣城的人子?还是修行求仙的张果老?已经无从辨别,也不需要辨认。因为,唐志军在西南深处寻找的早已不是“真相”,而是孙一通,是另一个唐志军。不谙世事,是英姿勃发的另一面;信口成诗的自由,正是指点宇宙的激昂。唐志军在状如母体的太空舱里,找到了孙一通。毒蘑菇致幻?吐出来就是了。这里不存在所谓的“幻想”,一切都是真实,举目都是自我。唐志军经由狭长的昏暗洞穴,走到了光亮洞口,犹如通过母体来到世界。在孙一通乘着麻雀飞升之后,唐志军重生。

在一九九零年的采访录像里,最后的问答,唐志军以沙子作比,颇有佛学意味。可惜,这只是他受困的开始。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顿,我们常会跳升一个维度去求答案,在外人听来有如顿悟的机锋,其实那不是答案,而是逃避问题的堂皇大话。一九九零年的唐志军,他把人类看得过分渺小,以至于只能寻求地球之外的世界给他新的方向,这些困惑都被标记在了电影的序幕后,一连串的新闻镜头蒙太奇句子。Life音频:00:0002:30他执迷于寻找生活中的不凡,也就是生命外的“他者”——外星人。三十年后,唐志军自述,他跟随他的“朋友”孙一通飞向了天际,也就是宇宙的边界,他回头,看到了宇宙的形态——双螺旋结构——生命的起源和真相。必须要注意的是,唐志军重生前求孙一通向外星人提问: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女儿求死的天问;这问题的答案,和寻找外星人的行为一样,是问题本身。唐志军看到了答案——生命本身就是意义。
<内嵌内容,请到原网页查看>
(《普罗米修斯》电影原声)
唐志军找到“答案”的媒介是孙一通,也就是唐志军自己,他西行探索,重新寻回的不是一九八零年代的“高光”,而是唐志军作为一个生命的主体性。唐志军重新以体面的打扮回归社会,他规训般的举止,似乎找回了丢失了三十年的“神儿”。其实,他写给女儿的诗,没能在影片里以言语的形态存在。这一设计,以无限的镜头后拉跃升维度,直至宇宙终点,直到显影双螺旋形态,这是又一次偷换概念,以堂皇的视听手法规避根本不该存在的父女故事。这也是全片唯一的失实之处,出于对院线观众的不信任,唐志军似乎必须要有个情感模型才能被理解,女儿的临终短信、墙面上的身高成长痕迹都是“存在”的能指,可惜其所指并未落在诗的言语上,唐老师的女儿到底没能来一回。这就和影片衔接过紧的配乐,以及没能抛弃的萝卜一样,都只是渲染情绪的飞碟。骑上驴背的一刻,我一直在期待着唐志军把萝卜扔掉,可惜,直到下驴都攥在手里,萝卜是被水冲走的。没有萝卜的驴,就像没有女儿的唐志军,也就是没有主动思考能力的观众,我们都活在《春节序曲》的忧伤自恋里。不过,唐志军和孙一通,还有那日苏、晓晓、秦彩蓉,甚至一起做出“终刊号”的杂志社全体成员们,以及精神康复中心的人们,他们在承受着当下社会“正常标准”的嫌弃鄙夷的同时,也成为了这部影片里最不同凡响的生命体。

这让我想起,在地坛公园某一个门前的广场,每到周日上午都会站满了合唱的人,他们被一个高亢的女声指挥着,情绪统一,歌声的颜色如血。在这黏腻的合唱过后,广场上总会出现孤零零一个中年女人,她带着小音箱和麦克风,跟着英语流行歌的鼓点自信地摇摆,偶尔笨拙地唱出歌词。彼时,常有过路的母亲借此教训她们的孩子说“这不就是自嗨吗!?”好在有诗,不论其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诗句都是庶民的话语;好在有过宇宙探索热,不论是民科还是自娱自乐,探索的精神都是庶民的求索。《宇宙探索编辑部》,能够提醒我们——有好奇心是好的。

图文编辑:普罗米修斯的小碗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