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及标题:新海誠監督『すずめの戸締まり』レビュー:「平成流」を戯画化する、あるいは〈怪異〉と犠牲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評:茂木謙之介)
继《你的名字》(2016年)、《天气之子》(2019年)之后,新海诚执导的电影《铃芽之旅》是继前两部电影之后的又一部娱乐大片,讲述了一对年轻男女修补在灾害中被切断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丝毫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
居住在九州宫崎的高中生岩户铃芽在上学途中遇到的东京大学生宗像草太,是代代掌管被称为“闭门师”的职能家族的末裔。闭门师要继承“家业”,用礼仪关闭全国废墟中存在的被称为“后门”的门。后门是“所有时间同时存在的地方”,与“死者前往的地方”“常世”相连,打开后会从里面出来“不好的东西”。偶然打开后门的铃芽,拔出了配置在那里的“要石”,让引起大地震的被称为“蚓厄”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虽然和草太好不容易成功关上了后门,但草太被变成猫的要石诅咒,与铃芽母亲的遗物——儿童用的椅子融为一体。为了抓住要石并取回原本的姿态,化为椅子的草太与铃芽一起踏上了从九州往东的旅程……
与迄今为止的新海诚电影一样,它采取了这样的架构:通过引用或轻触神话、传说、精神分析、文学、动画、电影等各种各样的文本,引出人们对“调查”和“解释”的欲望。即使在撰写本文的11月18日,人们在社交网站上也能看到相当数量的“考察”。也有很多观众为了投稿感想而重复观看电影,通过吸收多种要素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本文也和其他观者一样,以引用源之一为起点,从SNS上提及较多的围绕天皇的形象来评价这部电影。而且,到这里为止的阶段,诸位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对笔者而言,《铃芽之旅》并不是一部能够无条件地打出高分的电影,而且它本来就不是一部能够轻易评论的文本。在下想说,一旦它被捧成圣典,在下将尽力予以抵抗。
天谴论式的思考和被遗忘的死者
在各种各样的文本被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情况下,我想以村上春树的《青蛙君,拯救东京》作为讨论的起点。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名叫“蚓厄君”的非人类的存在,即将在东京地下引发巨大地震,这时,巨大的青蛙“青蛙君”为了压制它,向身为人类的片桐求援,引发大地震的“蚓厄君”显然对电影《铃芽之旅》中巨大妖怪“蚓厄”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但重要的是,直接引用伴随着重大的改变。在春树的小说中,面对妖怪之间的争斗,人是无法介入的,只需要对其中一方的应援,而应援本身也只是无意识的。
另一方面,在电影《铃芽之旅》中,草太在接近结局的场面“人心的沉重压抑着那块土地。一定还有那个消失后门打开的地方。”如上所述,出现蚯蚓的后门被设定为只要有人介入就不能随便打开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里的逻辑是,人的缺席会造成后门打开,结果这个地方就会遭遇灾难。这不仅仅是草太一个人的话。正如从东方的要石变成猫的“左大臣”要求自己“通过人的手恢复原状”,也就是要求再次将自己作为要石,来镇住蚓厄。从这一点可以明确看出,故事的前提是这样一种想法:巨大地震这一现象可以被人为所左右,神祇和妖怪也容忍这种现象发生。
也就是说,这里实质上展开的是一种“天谴论”的思考。天谴论的典型是关东大地震时的内村鉴三和东日本大地震时的石原慎太郎的言论,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给予人们的惩罚。天谴论者试图以灾害为契机对人们加以洗脑,不用说,这种言论是对灾区和灾民的恶意贬损,令人无法容忍。

根据观影特典“新海诚本”的介绍:“悼念场所”是本片的重要概念。将人为地失去人烟的产业性废墟,与因灾害而被迫切断人们生活的受灾地相提并论,进行同样的哀悼,其不可理解和麻木不仁之处自不必说,但在此请允许我想指出的是,其“悼念”的对象彻底限定在与人有关的土地上。天谴论认为,灾难会从与人的关系(即“人心的分量”)消失的地方发生,这种天谴论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人明白,地震总是会发生在人们居住的地方(可是九州南部、四国西侧、阪神、东京、东北三陆都曾因地震造成大规模受灾,影响历历在目)。可以说这是一种过于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
而且,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作为前提,我们才会意识到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其他被排除在外的存在。那就是灾难中的死者。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死者被排除在故事之外,这一点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铃芽为了寻找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丧生的母亲而哭泣(在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童年铃芽的哭声是最让我揪心的)。成为高中生的铃芽把母亲遗物的椅子交给了她。“不管现在多么悲伤。”“铃芽以后会好好长大的。”“所以别担心,未来并不可怕。”一边鼓励,一边放言“你今后也会喜欢上某人,也会遇到很多喜欢你的人”。在这个场景里,铃芽劝告幼年时期的铃芽,不要对母亲这个死者实践“不可能的丧事”(= 重复丧事的失败,继续丧事) ,而是要忘却这件事。回到现世的铃芽,记得曾经在常世迷路时遇到过母亲,但后来发现其实是遇到了未来的自己,小声说“重要的东西已经全部——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这些场景是将忘却正当化的极致表现,不如说是夺取死者的主体性而表现出来的极度无心无情的话语。在这里,死者被彻底地隐形化,被遗忘。(另外,可以说在电影中也存在着能够驳斥这种解释的表现形式。比如,草太的朋友芹泽在堆积着钢筋包的荒野,也许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地方,颇为麻木地说这里是“美丽的地方”,而铃芽表示不敢苟同,但新海诚对此只是轻轻触碰,决不做深入探讨。)
从开头的常世场景开始,通过描写渔船在建筑物上搁浅这种过于令人联想到东日本大地震的场景,也许我们可以揣测编导试图反对遗忘事件本身。但当将死者隐形化并忘却的处置方式与天谴论的思维相结合时,死者只会成为背负污名的存在。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煽情形式消费巨大灾害的极其暴力的故事,但在当事人中,围绕死者的表象问题尤为突出。(另外,这里说的是“当事人”,当然铃芽也是震灾的受灾者,从这个意义上,她也算当事人。但是,让她代理/代表灾害的当事人是否妥当,颇为可疑。而且,非当事者毕竟不能理解当事者,更不能剥夺其当事者性。在这一点上,本片的剧本可说是具有致命瑕疵的文本)

浮出水面的天皇与超自然力量迷信
前面提到的天谴论式思维,其根源在于所谓的“天人相关说”,即人为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善恶与自然现象有关联。在社交网站上,当日本网民对《铃芽之旅》进行探讨时,大家围绕“天人相关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外,“天人相关说”,与天皇拥有超自然力量加持的想法也有很大关联。例如,2019年10月德仁天皇登基大典时,皇宫上空出现彩虹,在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站上都传开了天皇有神力加持的言论。确实,不仅在电影《铃芽之旅》中,出现了大量似乎在描摹印证天皇言论的描写,小说版《铃芽之旅》也曾两次提到皇宫,在电影中,东京上空的铃芽直接掉进了皇宫护城河。光是这些,就足以说明《铃芽之旅》中充满了与天皇相关的表象。
下面我想加上一些“考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部电影的一部分特点就是暗示、引用或者隐约触及各种文本。对于天皇的相关话题,大部分也和其他作品一样,没有超出轻度参照的范围,而且基本上天皇和闭门师的联系并不是其主体,而只是两者的行为和言行相似的枝桠层面的东西,这一点需要事先声明。
竹内好说过:“天皇制的影响遍及日本各个角落,以至于一草一木都能探到天皇制的痕迹。” 或许就此穷究细节,彻底挖掘下去也是可以的,但考虑到这样可能带来盲目的肆意解读,所以我们暂且试着只提及与故事根基相关的部分。
在影片中涉及天皇的表象时,可以肯定的是,参照的文本是2016年8月明仁天皇的“关于天皇身为国家象征的使命的讲话”,即所谓的“天皇讲话”,或曰“录像讲话”。该“录像讲话”作为明仁天皇表示将在世退位的文本而闻名,其中包括明仁天皇本人对天皇“职责”的解释。这一点耐人寻味。在《铃芽之旅》成片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似乎正面体现了“录像讲话”要点的表达方式。
第一种是闭门师在关闭后门的时候,用“思念这里的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来表达。在废墟中,思念过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通过倾听他们的声音,打开关闭大门的钥匙孔,将土地归还给产土神。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本片与明仁天皇的言论的重合。
迄今为止,作为天皇的职责,我首先重视的是祈祷国民的安宁和幸福。与此同时,我认为有时站在人们身边,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伴他们的思想也很重要。(取自「录像讲话」)
也就是说,闭门师的仪式仿佛是在模仿天皇的象征行为,仿佛闭门师在超自然层面代理或代替了天皇的行为。这也可以认为是社交媒体将闭门师称为“里天皇”等的理由,但这一判断有必要从两点出发予以保留。
首先第一点是,这种说法不过是明仁天皇发表的言论而已。至少倾听人们声音的存在方式是所谓“平成流”天皇主义的特征,这与其说是明仁天皇一人的行为,不如说是美智子皇后、宫内厅相关人士和媒体的反应等综合性产物,可以说,这正是填补象征天皇“象征”内涵的工作。另外,皇室亲自参加祭祀的动向在平成时代更加明显,而且宫中祭祀大多是近代复活或新兴的“人造传统”,很难一概而论地说这是皇室自古以来就有的义务。这与影片通过众多文书所展示的闭门师的“传统”存在方式不一致。
第二点是本文中“倾听声音”的虚伪性。草太让铃芽代为关门时说: “这里曾经有过的景色。这里曾经有过的人们。这种感情。想着这些,倾听他们的声音。”。是的,只是“想”而已。在那个时候,里面描绘的景象和人们的声音就有可能是铃芽的幻觉。这样想来,最终在常世幻视东日本大地震灾区时,人们的声音都是正面的(“我走了”“我开动了”“去吧”等等),就比较能够说得通。如果是追踪还原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没有悲伤、痛苦和愤怒的声音,但如果是铃芽自己心中的幻影的话就可以解释了。这也可能作为叙述者的问题浮出水面,所以将在后面叙述。
再附带一句,倾听声音与天皇有关,在电影中,在皇居地下关上东京后门时,无法完全识别掉落地点的铃芽无法清楚地听到东京历次地震受灾者们的声音,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在小说《铃芽》中被表现为“太遥远”的声音)。在皇居的地下关闭后门时,之所以听不到声音,首先可能的解释是不知道那里是哪里,这种解释会证明“声音”是虚妄的。如果实际上铃芽能够听到那里流淌的声音而没有听到,那么这种解释就成立了——天皇、皇族是听不到声音的存在。也就是说,天皇作为一种超越闭门师的超自然主体被召唤进来,闭门师就被包含在这个序列之中。
虽然有点画蛇添足,但对于包括闭门师在内的登场人物与天皇的序列关系的可能性,登场人物的“岩户”和“宗像”,还有“大臣”,“左大臣”的故事中的命名似乎也有必要指出。原本天之“岩户”和“宗像”大社都在记纪神话中有相关记述,确实具有支撑天皇(制)的一面(果然只能说是表层的、因而平庸的接纳… …)与此同时,从“左大臣”这个东方要石的名字来看,可以预测被称为“大臣”的西方要石必然是“右大臣”,结果就会引发人们对君临其上的天皇的想象力。
说起来,本片在神话和历史的基础上借用名字,同时让在序列意义的框架中统御角色们的“有超自然力量的天皇”的想象力浮出水面并得到增强,以此作为故事的背景。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可以被评价为支持明仁天皇阐述宗教权威性的言论的电影。(关于现代日本社会的超自然化天皇形象,请参阅2022年出版的拙著《社交网络天皇论》)

“家庭”、“情绪劳动”与被牺牲的异类们
现在,作为文本的参考来源,让人意识到与天皇的“视频讲话”之间的联系的另一件事是:在这个被统御的框架中实际从事作业的闭门师,被认为是宗像家“代代相传的家业”,它被描绘成“仅靠这些无法维持生计”的东西。前半部分描写的是家庭问题,后半部分确认了所谓“情绪劳动”问题的浮出水面,但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与明仁天皇言论的相关性。在“视频讲话”中,明仁天皇提到了“剩下的家人”,显示出了以自己的血统继承皇统的欲望。在减轻天皇负担之际,以祭祀为首,“忙碌的天皇”这一形象从宫内厅传出,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这似乎暗示了天皇和闭门师的联结,他们正在做着“重要但无人看到”的事情。可以说,这呈现出了一种构造,即天皇的职能由处于这种秩序之中的人们来支撑。
这种思想的背景是什么呢?笔者想起了1980年代以后玄学语境中的一种说法,所有日本人都肩负着拯救地球的使命,并拥有支撑这一使命的内在超自然力量等言论。(详情请参阅妖怪怪谈研究会编著的《〈妖怪〉与民族主义》一书,2021年出版)。闭门师所覆盖的锁门范围一直局限于“日本”,这是一个非常乡土式的故事,它也可以被定位为一种民族主义想象力的流露:以天皇为中心的超自然体系,是由置身其中的每个人支撑的。
此外,家庭和情绪劳动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故事情节本身。
在这个故事里描写了各种形态、各种状况的家庭,特别是铃芽和她的收养者环之间的关系是故事的中心线。铃芽在地震中失去了独自抚养她的母亲,环对铃芽说“成为我的孩子吧”,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和草太的旅行而动摇,在“左大臣”这个异类的介入下得到解放,从而重新构筑起来。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被修复起来的,草太和铃芽的关系大概也是这样。与此相反,被抛弃的是与“妖怪”的关系。在草太被变成椅子的场景中,铃芽问大臣“你会成为我的孩子吗?”,而大臣回答的场景是驱动故事情节的重要场景,但结果大臣遭到了铃芽的拒绝“我没能成为铃芽的孩子”说完又变回要石。在这里可以看出从传统家庭框架中排除“妖怪”的构造。
另外,关于情绪劳动,可以说,大臣原本就被强加了把蚓厄绑在大地上的“劳动”,现在已经摆脱了这个角色,获得了自由,而铃芽则根据自身的情况再次强加了这个“劳动”。于是,这又与前述被遗忘的死者的问题重叠起来。这是一种排除了神祇和妖怪的结构,“不被当成人对待的家伙”的主体性得不到尊重,成为牺牲的对象,这种不平衡被揭示出来。
从以上讨论来看,我们只能把它看作这样一个故事:在以天皇为顶点的高仿“国家神道”框架的扭曲的超自然机制的驱动下,不被当成人的异类们受到侵害。但是最后我想再提出一项对本片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可能性,这也真是本文的最后一项。这就是上文稍微提过的叙述者的问题。

对记忆的另一种解读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铃芽之旅》里都遍布着方言。其中,只有在日本各地旅行(与天皇巡幸的印象相通?)的铃芽和居住在东京的人使用所谓的“标准语”,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但在这里,我想将其视为表示铃芽作为讲述者的标志。
刚才我说过,铃芽在关门时看到听到的人们的生活、形象、声音等记忆,其实是不是虚妄呢?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得到证实。那是在铃芽拔出被当作要石的草太时,与草太共享记忆的场景。在此暗示草太对铃芽抱持著某种正面的印象,不过在这时,画面上出现了草太的视点不可能看到的,草太与铃芽并肩而行的场面。这可以说是改写他人记忆的场景。反过来看看小说《铃芽之旅》就会发现,其中以铃芽的第一人称展开了故事,进行故事统御的叙述者的粗暴性被前景化了。
比如,铃芽在中途说“喜欢”草太,但是当她想起自己当初是因为把草太变成椅子而感到内疚才和草太一起走的时候,那真的可以用“喜欢”来概括吗?倒不如说铃芽是作为自欺欺人的讲述者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彻底地从非常角度来欣赏本片,那么这个文本就有可能产生“改写自我和他人记忆的故事”的批判性。例如,如果将其从引用材料的“视频讲话”生发开去审视,或许可以加深对明仁天皇“站在人们身边,倾听他们的声音,贴近他们的思想”这一宣言的理解。实际上,被明仁天皇站在身边,倾听其声音,贴近其思想的民众又有多少呢?如果可以明确这一言论的空洞性,那么可以说《铃芽之旅》作为天皇电影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额外说一句,在小说《铃芽》中,叙述者从铃芽变更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在东京上空不顾一切地刺入要石,铃芽坠落地面,与此同时,正文中第一次了对皇宫的描写。这也是该文本被设定为围绕天皇的故事的决定性证据)但是,这种极其脆弱的读解方法如何实现,以及它是否超越了本片文本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疑问。
笔者的境遇可能比较特殊:在2011年3月10日因故离开东北三县、在灾后被东京天龙人等外地居民散步的各种令人心寒的言论气得咬牙切齿,如今在东北地区生活工作。上述尝试解读的内容,也可能因此显得有些过度。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读者留言雅正。
 (本文作者茂木谦之介)
(本文作者茂木谦之介)作者简介:茂木谦之介,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部文学研究科准教授(日语的“大学院”相当于内地大学的研究生院,“文学部”相当于内地大学的“人文学院”),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化史和表象文化论。单独著作有《社交网络天皇论:流行文化=超自然主义与现代日本》(讲谈社,2022年出版)、 《表象天皇制论讲义: 皇族・地域・传媒》(白泽社,2019年出版)。与他人联合编著的著作有《日本学的教科书》 (文学通信社,2022年出版)、《妖怪与民族主义》(青弓社,2021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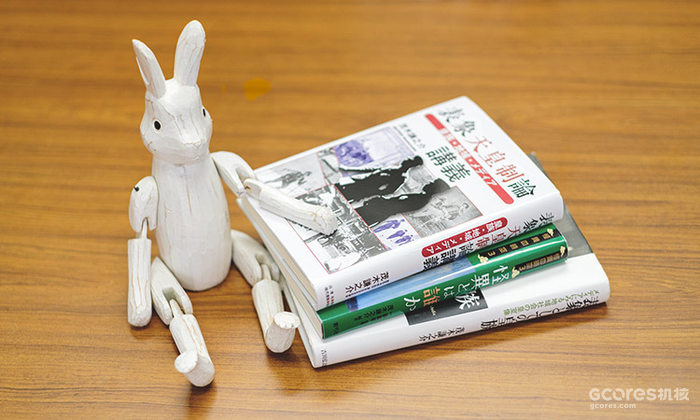 (茂木氏的部分著作)
(茂木氏的部分著作)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ufabet
มีเกมให้เลือกเล่นมากมาย: เกมเดิมพั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ครบทุกค่ายดัง


